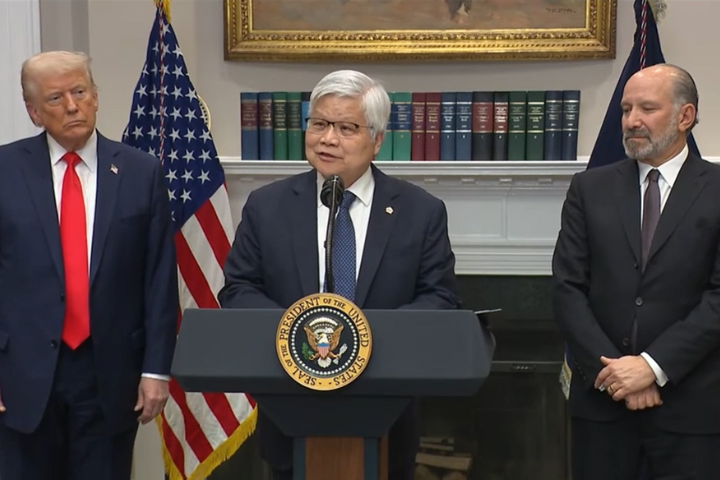黃靖麟/國立大學教師
2025年7月26日投票,由民進黨主導,訴求「反共護台」的大旗,針對24位國民黨立委與新竹市長高虹安的大規模罷免案,最終以全數都不同意罷免而失敗收場。這場「大罷免」不僅未能撼動藍營基本盤,更反映出台灣選民結構與政治情緒的複雜「負面黨性」(Negative Partisanship)現象。
筆者認為「負面黨性」最有可能是民進黨的大罷免失敗的主要因素,謹分析如下:
一、「負面黨性」對投票態度的影響
「負面黨性」指的是選民並非直接支持某一政黨,而是因為厭惡或排斥對立政黨而做投票選擇。這種「討厭的力量」在選舉乃至罷免運動中尤其明顯,而且似已逐漸形成台灣民主、投票的關鍵變數。根據學者研究,2020年總統大選時,超過40%選民對兩大政黨之一持有負面看法;而這種仇恨動員的情感極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與負面黨性,會在選舉與公共事務中不斷增長。民進黨高估社會對國民黨立委不滿,卻低估了「藍白合」(泛藍與台灣民眾黨)組織動員的實力。罷免方動員侷限在深綠基本盤,難以擴展至中間選民,反倒激發基層組織戰及對罷免程序過於政治操作的反彈情緒。
二、中間選民「討厭在野、也討厭執政黨」的負面動機
中間選民與沉默選民(silent voters),多對過度政治化行動反感。部分原本對國民黨立委表現不滿的選民,最終選擇冷淡、觀望或投反對罷免票,顯示其並非出於對DPP高度認同而投票。因此,是對民進黨及其側翼罷團的「負面動機」,反噬了罷免案本身。
三、高門檻的罷免制度設計
選罷法在修正罷免門檻時,雖然將原先的極高門檻降低,但連署及25%投票及同意必須大於不同意票數,仍有人認為此現行罷免門檻過高。特別是居於提案方必須進行負面動員,而能將「負面動員」情緒,轉化為具體有效支持的選票,07/26的投票顯然提案方無能為之,導致結果全面失利。
四、罷免方「同溫層效應」與論述空轉
民進黨導向的罷免訴求未能連結日常民生,訴求侷限於「挺台反中」政治標籤,無法感動對象選區的多數選民,當然罷免吹起的氣球成效反而泡沫化。
「負面黨性」並非台灣專利。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雖然拜登(Joseph R. Biden Jr. )當選,但輿論多認為是「川普打敗川普」(Trump defeated himself),而非拜登打敗川普。太多美國選民因為厭惡Donald J. Trump,最終選擇支持拜登,也非出自選民高度認同拜登政策。
07/26這場民進黨主導的大罷免大失敗,再次證明台灣社會的「負面黨性」,已到高度極化階段。但只用「討厭對方」當作動員主力,不僅無法有效翻轉選舉結果,反而可能引發反作用力,讓中間與冷漠選民更反感過度對立的政黨操作。無論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若無法超越仇恨動員,回歸理性政策與公共利益訴求,筆者個人認為都很難在未來爭取更廣泛認同與信任。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