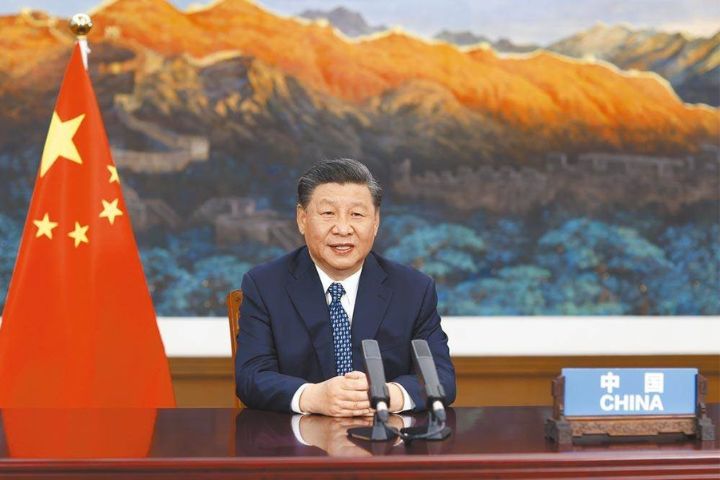張瑞雄/台北商業大學前校長、叡揚資訊顧問
人工智慧的浪潮已席捲全球資本市場,從矽谷到華爾街,從政府政策到企業戰略,無不圍繞著這場看似無可抗拒的技術革命。當市場上浮現出一片對未來的狂熱憧憬時,也有理性聲音開始質疑:這真的是一場真正的科技突破,還是一場披著創新外衣的泡沫狂歡?
AI的確改變了許多行業的運作方式,也提供了令人振奮的潛力畫面。但若僅憑市場股價飆升與資金蜂擁而至,就斷定這是歷史性轉型的開端,恐怕為時過早。
根據最新的市場分析,AI相關企業的資本支出與估值已達到歷史新高,單是前十大科技公司便吸收了超過一半的市場投資。若將這些企業從指數中剔除,美國整體企業盈餘表現近乎停滯。這樣的集中投資現象,彷彿重演了19世紀的鐵路狂熱與1990年代的網路泡沫,而AI這次似乎來得更猛烈。
投資人心中真正的問題不在於AI技術是否有價值,而在於這些價值是否已被過度預支。企業如Nvidia、Meta與OpenAI固然在財報中展示亮眼成績,但仔細檢視會發現這些成績大多來自基礎建設供應鏈,而非真正來自AI應用所帶動的生產力提升。這就如同賣鏟子的在淘金熱中獲利,而非實際找到金礦的人。
更值得警惕的是,AI並未顯著提升整體生產力。近三年來,美國的勞動生產力年增率僅約1%,仍延續過去幾十年來的低迷趨勢。儘管有樂觀者主張科技紅利需要時間發酵,但現實卻是企業多數AI應用尚停留在語言生成、圖像識別或客戶服務等領域,真正能改變產業效率的應用仍未普及。若AI的主要用途是讓人們更快找到網頁摘要、減少客服人力、或是自動生成行銷文案,那麼它對GDP的貢獻恐怕難以支持如此龐大的投資。
而這場資本競逐的代價,已逐漸浮現。AI資料中心建設成本驚人,根據研究估算,至2030年,全球需投入近七兆美元來維持AI運算需求。這些資料中心不僅硬體折舊快速,還消耗巨量電力與水資源,加劇能源價格與通膨壓力。在經濟尚未受惠的情況下,這樣的投入反而成為另一種拖累。
AI的經濟效益也存在結構性問題,所謂「供應悖論」指出,AI越容易學會的任務,經濟價值往往越低。像是文案撰寫或簡單查詢類任務,因知識門檻低、樣本大量充足,AI容易取代,但這些工作本就報酬有限,無法支撐巨大的資本報酬需求。反之,醫療、工程或法律等高門檻領域,因專業知識難以量化,AI進展有限,真正的「殺手級應用」仍難現蹤。
目前科技巨頭的營收成長,很多是透過AI強化平台黏著度,攫取原屬他人產業的收益。例如Google以AI摘要保留用戶在搜尋頁面,廣告收益自己賺,卻犧牲了原始網站的流量;Meta透過AI演算法引導用戶消費更多內容,廣告營收提升,卻讓其他出版業者收入縮水。這樣的利益轉移,並未創造新增產值,只是將市場份額從一方轉移到另一方。
這樣的結構性偏斜,對整體社會與經濟也帶來長遠風險。當資本回報集中於少數科技公司,社會貧富差距擴大,政治極化與社會不安感加劇。若AI持續取代中產階級知識工作者,而新增工作集中於低薪、低生產力產業,如照護與勞力服務,那麼整體經濟的結構將出現下沉現象。
更令人憂心的是,這場泡沫的破裂或許並不遙遠。已有研究指出,高達九成以上的AI投資企業並未產生實質回報,許多初創公司仍嚴重虧損,甚至連OpenAI也預估最早要到2029年才可能實現盈餘。而若未來再爆出幾起資料濫用、智慧財產侵權或AI誤導致人傷亡等事件,將如同刺破泡泡的針,引發市場全面信心危機。
這並不代表AI毫無前景,歷史上,鐵路泡沫、網路泡沫皆曾重創市場,但最終也孕育出改變世界的基礎建設與企業。但投資者與政策制定者若不保有清醒頭腦,未來的回顧將不會是創新紀元的開始,而是一場貪婪與盲從的哀歌。
泡沫何時會破,沒有人能預言。但當所有人都相信未來只有上漲的可能,或許正是該警醒的時刻。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