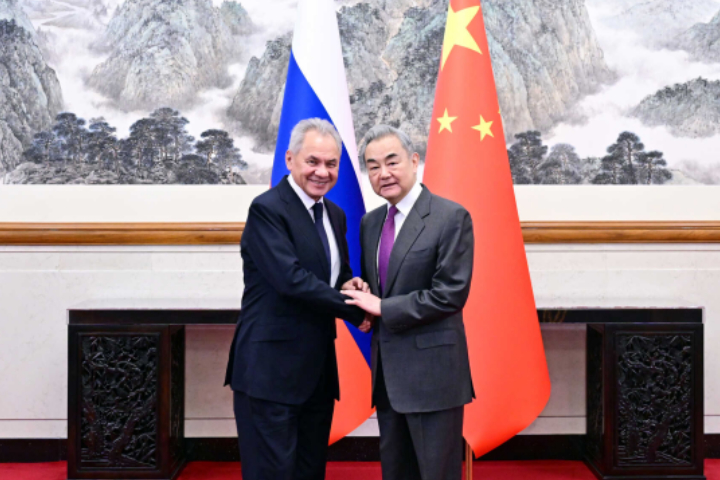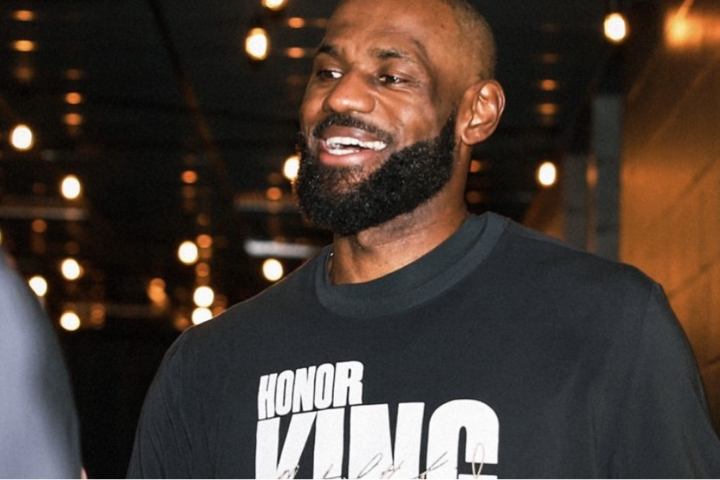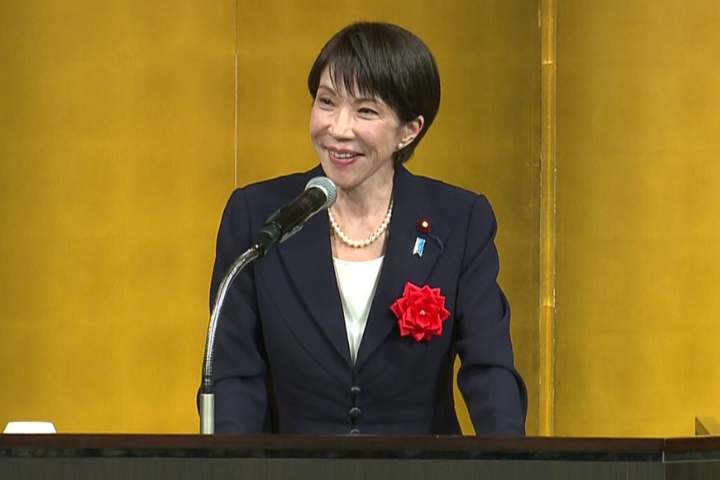魯云湘/戰略智庫研究員
1953年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第18屆理事會決議,批准成立「台北飛航情報區」(Taipei FIR),並由當時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CAA),負責該區域的飛航情報與空管服務。半世紀以來,這項非國家實體的技術服務安排,不僅奠定台北 FIR 的法理基礎,也讓它在全球民航安全體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然而,自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並於1973年喪失ICAO會員資格後,北京方才獲得中國代表權。面對失去「正式席位」的困境,台北 FIR 仍須承擔兩大挑戰:一是如何在缺乏代表權的情形下繼續提供飛航服務;二是如何對抗北京單方面規劃並啟用M503、W121/W122/W123等航路的程序與法理爭議。
首先,1944年《芝加哥公約》確立「安全優先、合作共治」之全球航空治理理念。ICAO隨即透過《Annex 11》等技術文件,將全球劃分為數十個飛航情報區,並委託具備空管能量的國家或地區執行相關服務。1953年以來,台北 FIR 承擔包括氣象通報、航路協調、事故救援在內的國際委託職責,其本質在於「技術服務」而非「主權移轉」。
儘管1973年失去ICAO正式席位,北京當時尚未取得代表權,但為飛航管制服務,便已劃設上海、廣州、昆明等多個大陸地區的FIR,由此可知飛航情報區的運作,依賴ICAO對既有空管單位的「授權延續」與技術能量,而非會員身份的變動。有鑒於此,台北 FIR 於代表權變動後,依舊保有既有管轄與服務職責,其運作基礎並未遭受動搖。
因此筆者先前曾誤稱,台北無論以何種名義,皆非 ICAO 正式會員,且無立場與北京在該框架下正式協商此類爭議,為免誤導讀者,特此更正,並感謝各方指正。事實上,台北 雖非ICAO正式會員,但仍具非國家實體的獨立技術委託地位與協商空間。
其次,自2007年起,北京方面提出M503航路規劃,並延伸衍生W121至W123等銜接航線。過程中,CAAC(中國民用航空局)邀請FAA(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專家對M503進行安全可行性評估,並將該報告納入ICAO多邊審查資料。
2015年,於南海航路區域工作小組(SCS‑MTFRG)會議上,CAAC再次提交FAA報告、香港FIR與台北 FIR 的協調紀錄,以及IATA(國際航空運輸協會)意見,最終獲得集體技術審查通過。當時有賴於前總統馬英九,基於國內輿情考量,透過兩岸民航協商機制與北京交涉,換取以下讓步:
1. M503北向段向西偏移6浬,與台灣海峽中線保持安全距離;
2. 暫緩啟用M503北向段及W121/W122/W123等銜接航路,以便後續進一步協商。
隨著兩岸協商機制逐漸降溫,北京於2024年1月,宣布取消M503南下航路的西偏飛行安排,並同時啟用W122及W123由西向東飛航的新航線協議。此舉意味著,北京已不再顧慮2015年協商所定的安全讓步,進一步顯示其在華南沿海航路規劃上的自主意圖。
面對北京單方面優化M503、W121至W123航路、挑戰程序規範,台北可採取多管齊下策略,除向ICAO提出差異聲明,發布爭議航路的NOTAM,更可結合法律、技術與外交渠道爭取國際支持。然而,《SCS‑MTFRG》2015年報告第1.8條明文禁令:航機不得在未經空管許可下偏離M503航路,也不得向東偏離;如要偏航,必須提前申請協調。換句話說,除非大陸方面先出現飛航違規事件,否則台北難以依此條款提出程序異議。
台北 FIR 自1953年以來,一直是全球航空安全網絡的關鍵節點。即使在缺乏正式席位,以及面對程序限制的雙重夾擊下,仍可在法理與技術框架內爭取權益。展望未來,唯有在嚴守ICAO標準、靈活運用協商機制,並敏銳回應地緣政治變局的前提下,才能在挑戰中尋求突破,真正維護中華民國在東亞上空的合法地位。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