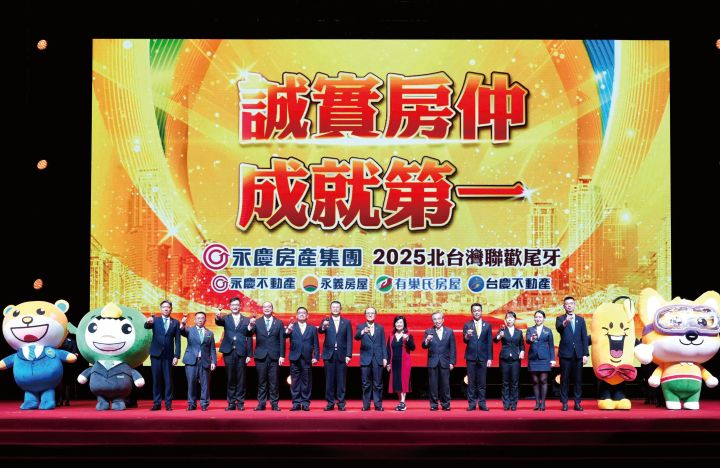張瑞雄/台北商業大學前校長 叡揚資訊顧問
在人工智慧被譽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增強腦力的技術」的同時,世界也分裂成兩種截然不同的節奏。一邊是掌聲與獎章,宣示這是繼蒸汽與電力之後的新文明轉捩;另一邊,學生、工程師與藝術家拒絕使用AI,堅持用雙手與思考維持人性的觸感。當科技的速度超越社會的呼吸,我們不得不問:「AI究竟是在創造新的智慧,還是在放大人類的焦慮。」
黃仁勳說「這不是泡沫,所有GPU都在運轉」,那是一種工程師的信仰,相信算力即真理。他看見的是未來每一刻都將被AI滲透的生活,是千年一遇的智慧革命。這種樂觀或許真誠,但也隱含著技術中心主義的傲慢。當一切都能被加速,我們是否仍知道加速的方向。
但AI會說話,不代表它懂世界。機器能翻譯百種語言,卻不理解一個詞背後的情感與歷史。人類花了數百年才學會「理解」與「共情」,而AI目前仍停留在模式的模仿。「飛機能飛,但不是像鳥一樣飛」,這句話道出了AI與人類的根本差異。當社會急著用參數規模定義智慧時,科學家卻在提醒我們真正的智慧,不只是速度與資料,而是理解與倫理的結合。
這樣的技術信仰與懷疑,也在社會底層形成了對比的風景。一位16歲的學生拒絕在作業中使用AI,因為她相信學習的意義在於思考,而非生成答案。軟體工程師寧願關掉所有AI功能,也不願讓程式判斷他的創造。設計師在作品上印上「not by AI」的標章,成為人類創造力的宣言。這些看似微小的抵抗,實則是一種文化上的求救訊號,當智慧被量化成模型輸出,人類是否仍有存在的價值。
AI不僅改變勞動型態,也正在重塑經濟結構。根據分析,AI的自動化可能取代高達7%的工作,尤其是中產階級的白領職位。當程式設計師與審計員被演算法取代,社會的消費動能將被抽離,經濟的血液將不再循環。面對這樣的未來,矽谷的領袖開始談起「全民基本收入」。這看似理想的分配構想,在現實中卻像一場巨大的幻覺。若每人每年領取一萬美元,美國政府將需要三兆美元的支出,而這樣的金額幾乎吞噬了整個預算。所謂「科技造福人類」的承諾,似乎正在轉化為「科技吞噬人類」的焦慮。
「科技讓我們變成能做任何事的人,但我們仍未學會該做什麼事」,這句話在今日顯得格外刺耳。AI的進步確實驚人,從醫療影像判讀到自動編程,無不展現人類創造的輝煌。但這份輝煌若沒有倫理與制度的支撐,便可能轉為新的壓迫。當公司強迫員工使用AI、政府鼓勵AI教育、學校以效率取代思辨,我們或許正悄悄把思考的權力交給演算法。當孩子不再寫作,只會「提示」;當員工不再決策,只會「生成」,人類的心智將在無聲的依賴中鈍化。
這不只是技術議題,而是文明的重點。AI的確可能成為解放的工具,也可能是監控的枷鎖。「技術進步是指數的,社會適應卻是線性的」,當AI以光速前進,而法律、教育與倫理仍在原地踏步,世界便出現時間的錯位。這種不對稱不僅造成經濟不平等,也產生知識與文化的斷層。那些能駕馭AI的人將掌握權力,不能者則被迫依附。AI不只是智慧的革命,更是階級的再造。
在這樣的轉折點上,我們或許該重新定義「智慧」這個字。它不只是機器的能力,更是人類的自省。真正的智慧不在於AI能回答多少問題,而在於人類是否還會提出問題。當AI能預測我們的選擇,我們是否還能選擇自己的人生?當AI能創作音樂、畫畫、寫詩,我們是否還願意用笨拙的手去創造獨一無二的不完美?
「未來就在今天,但永遠不會有確定的那一天」。這句話或許正是AI時代的註腳。科技不會停下,人性也不應退場。面對AI的浪潮,與其恐懼被取代,不如學會共存;與其盲目崇拜,不如勇於懷疑。AI可以讓我們更強,但唯有人類的誠實、感受與責任,才能讓這場革命不變成泡沫。
當機器越來越聰明,真正的挑戰,是我們是否也能變得更有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