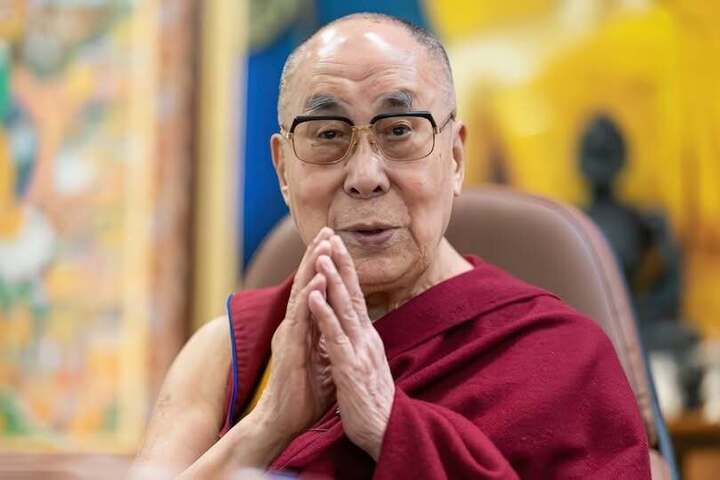李貴敏/現任律師
台北政壇近來傳來一個刺耳的數字:七千億元。財政部日前表示,國安基金名義規模雖為5,000億元,但實際可動用資金僅約2,000億元,因為其中有三千億元需向公勞保等基金調度,但這些人民的退休與養老儲備多已投入運作,因此現在期望透過公股行庫籌措資金,再加碼7,000億元。這番話,擺明了就是要告訴我們:即便臺股已然站上兩萬七千點的天際線,總市值逼近四十兆元,政府仍亟需用更龐大的國家資源,來支撐這份高處不勝寒的「盛世」。
國安基金自 2000 年成立以來,其宗旨原本是針對「非經濟因素」對市場的衝擊,以維持資本市場的安定,確保國家安全。然而,歷經八次護盤,特別是近期的幾次,國安基金的角色已然偏離了初衷,從應對經濟危機的「戰時工具」,逐漸轉變為提振景氣、穩定盤勢的「控盤工具」。當前股市屢創歷史新高,卻傳出要打破設立規範,大幅擴編資金上限,這已然違背了其「出事之後,才進場救援」的基本原則,更可能將政府的干預變成一種常態化的市場扭曲。
回看史上最長的一次護盤,2022年7月至2023年4月,國安基金以逾一成五的帳面報酬收場,表面亮眼,爭議卻未因此消散。當時國際政經不穩、通膨升溫、升息陰影籠罩,台股重挫;而在進場初期的七至九月,依金管會統計,境外投資人與外國自然人累計淨匯出高達一六三億多美元。這條資金軌跡說明了殘酷的現實:當國家隊入場承接、價格跌勢緩和,外資便得以在較有秩序的環境中降低部位、優化虧損,待風險釐清再伺機回補。護盤接住的是信心,同時也替急欲降風險的國際資本鋪出一條更平順的出口。
護盤在這種時刻進場,固然可以「接住信心」,也等於替急於降風險的國際資本提供一個更有秩序的出口。這種現象並非臺灣獨有,離我們不遠的南韓,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動用穩定基金,同樣是為外資提供了更優渥的退出條件。當時外資恐慌性拋售韓元計價資產,政府的介入雖然穩定住了金融體系,但客觀上卻是讓外資得以在市場回穩、股價反彈時,選擇性地將資金調度至他們認為更有利可圖的國際市場。南韓的經驗,赤裸裸地揭示了政府的護盤資金,實質上成了國際熱錢安全離場的工具。
今年第九次護盤則像把教科書演示了一遍。四月「對等關稅」風暴來襲、台股暴跌,國安基金授權進場,當月外資仍選擇淨匯出5.48億美元,市場顯示危機當下的第一反應是撤退。隨後關稅暫緩九十天、恐慌消退,外資在五月單月大幅回流126.68億美元並連續數月淨匯入,科技權值股一路推高,指數節節攀升;到了八月,指數觸頂、雜訊再起,外資再度轉為淨匯出13.66億美元。這不是道德評判,而是跨市場資產配置的冷規則:政策資金把地基灌漿、把灰塵掃淨,最先進門與最早離場的,多半是行動極快的國際資本。
因此,當政府在高檔行情中仍堅持不退場,還要把融資上限再往上推七千億,社會當然會有疑問。若真如官員所言,五千億的法定上限已與九十兆級市值不相襯,那該做的是重申「啟動—退場」的明確門檻、把「非常時刻」的定義寫到不能再模糊,而不是把「市場永遠充滿不確定」當成永久留守的理由。
這並非要否定國安基金的存在價值。二十五年來,它確實在幾度驟變中穩住了社會情緒,這份功能值得保留;但功能越是重要,紀律越要嚴謹。法條寫得白紙黑字:重大事件、資本市場失序,方得動用;任務達成,便應適時處理標的。今天我們該問的不是「能不能再多借七千億、一兆元更好」,而是「何時撤、怎麼撤、誰來背書撤場紀律」。一旦退場變成政治成本、進場變成政治快感,護盤也就不再是護國,而是護一張漂亮的指數曲線。
如今,國安基金已然背離了「救市」初衷,偏離了「維穩」宗旨,成了一般投資基金,成了維持政治形象的工具。政府用納稅人的錢成立基金投入股市來護盤,作法必須慎重,如果這種國家干預的行為,不小心成了外資利用的工具,使得國家銀彈成為國際資本的「安全門」和「提款機」,那才真是得不償失。畢竟,這份對國家干預的迷信,最終將損害臺灣經濟的本質。當我們為眼前的指數高歌喝采時,請不要忘記,這場由國家買單的盛世,最終的贏家,很可能永遠不是我們臺灣的百姓。
這份沉重的憂慮,值得每一個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