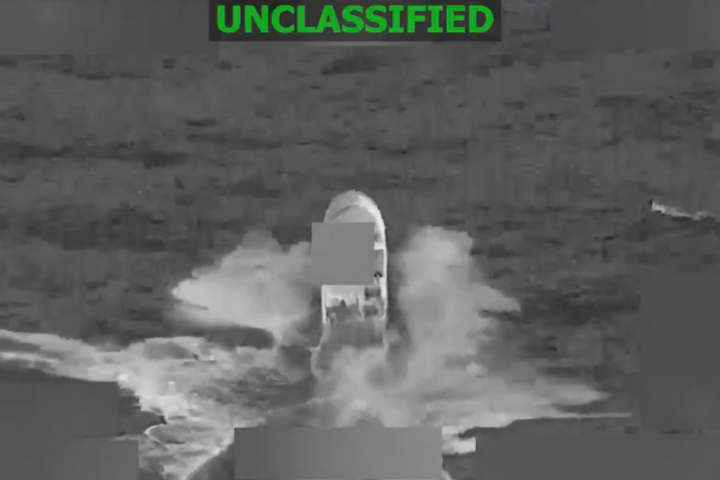廖雨詩/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總統在將官晉任典禮上高調讚揚「從二兵到中將」的勵志故事,表面上是階級流動的佳話,實則是體制失衡的遮羞布。台灣現役兵力約15萬,卻養出57位中將、明年還要衝到60;相形之下,以色列國防軍現役17萬、參謀總長「中將只有一人」。這不是誰比較會說故事,而是誰比較誠實面對結構。當兵源補不起來、戰鬥單位缺員成常態,我們選擇的對策竟然是「再升幾顆星」。把升官當解方,本身就是病徵。
問題的核心不在「頭銜太多」4個字,而在錯誤激勵已經寫進制度。今天的升遷文化獎勵的是「少犯錯」,不是「敢破題」。在單一明確敵手的安全環境下,我們準備了30年,卻仍由外國顧問一遍遍替我們畫缺口:動員速度、後備整建、彈藥存量、分散指管、複合演訓。為什麼?因為「不做新改變就不會出事」,宦途更穩當。結果就是:招不到兵,就升將軍;基層榮譽感被透支,戰力當然被掏空。
更現實的代價在財政與社會信任。將官的薪俸與退撫是長期承諾,當「頭銜膨脹」吃掉訓練與維保的邊際預算,部隊妥善率與彈藥填充率就只能在報表上好看。退役之後,一些人轉身坐上台北球場、欣欣客運等公私部門董座,薪酬疊加退休俸,合乎規章卻不合公道感。基層官兵看在眼裡,怎會不懷疑:原來軍旅最高價值,是離開軍旅之後?
這種邏輯在民間企業早就被視為管理荒謬。公司從60萬人裁到15萬,管理層理當等比例瘦身;國軍卻反其道行之,把將官層做大。結果是決策鏈條更長、責任更薄、速度更慢。老馬時代都還裁過將軍——那時兵更多;今天兵更少、將更多,卻還要告訴社會「這是專業」。若連最基本的「管理跨度」都說不通,談什麼聯戰整合?
有人會說,「高階軍職需要資深者,有經驗才能指揮作戰。」但經驗不是年齡,膽識不是年資。蔣介石擔任委員長30多歲固然是時代特殊,但也提醒我們:戰場從不頒發老年福利。真正的專業,不是把職務當養老金,而是把每一級晉升綁在可驗證的作戰成果上。今天我們準備對付同一個對手超過30年,到了現在卻還要靠一位法律背景的領導人來教部隊怎麼打仗——這不是總統的問題,是軍方自我失能的證明。
最該被追問的是總統與國防部長:為什麼你們仍相信「升更多將領」能解決問題?如果一家企業年年輸給競爭者,董事會會換總裁,而不是幫他加頭銜。軍隊也一樣。無法交出戰力指標的人,就該離位;能把部隊妥善率、演訓時數、紅藍對抗成績與後備整建帶上去的人,無論年齡與出身,都該被破格拉上來。這才是用人唯能,不是用人唯星。
更殘酷地說,軍中榮譽的消失,正是將星氾濫的副作用。當年輕軍官發現,最安全的途徑是別冒險、別創新、別承擔——因為出事就邊緣化,沒事就升官——最後留下的只會是會走程序、不願打勝仗的人。然後,我們再用更多的勵志樣板來安慰社會:看,從二兵也能當中將。是的,可以;但若整體戰力往下滑,這故事就只剩宣傳價值。
改革的方向其實很簡單:把「升遷」改成「戰力契約」。每一次晉任,都必須伴隨公開、可核的承諾——妥善率到多少、彈藥填充到多少、合成演訓與聯合火力到什麼水準、後備點名與動員時程縮短多少。做得到,頭銜是責任的徽章;做不到,頭銜就是撤換的起點。
同時,建立嚴格的「旋轉門」與冷卻期,堵住退職後的灰色誘因;把資源往訓練、維保、無人化與分散指管傾斜,讓將官結構回到與兵力相稱的比例;創造一條真正開放的「任務—專長」晉升軌,讓敢於承擔風險、擅用數據、懂聯戰的校級軍官得以橫向突破,而不是一輩子排隊等年資。
台灣不是沒有好軍人,而是好的激勵被壞制度消音。把升遷當答案,就是把失靈的指標升級成失靈的戰略。戰場不看星星,只看能不能打贏。把每一顆星都變成可驗證的勝仗承諾,國軍才會從「升官學」回到「作戰學」。届時,「從二兵到中將」不必再被包裝成奇蹟——它只會是健康軍制的日常風景。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