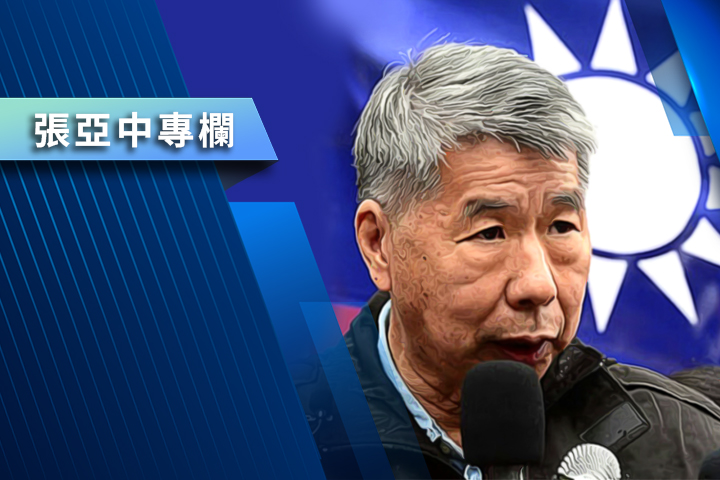張亞中/孫文學校總校長、中國國民黨主席參選人
日本投降至今已八十年。八十年來,戰爭受害國與無數受害者每一年都在期待,日本能夠勇於承認錯誤、表達真誠懺悔。然而事實卻是,八十年間日本多以敷衍姿態面對,甚至愈走愈遠。從天皇的《終戰詔書》到歷任首相的「變調道歉」,日本在歷史責任上的閃躲,已經讓亞洲鄰國的耐心逐漸耗盡。今年適逢戰後八十週年,日本首相石破茂乾脆連「戰後首相談話」都取消了,連象徵性的姿態都不再保留。這種態度的根源,在我看來,正是因為當年日本天皇在宣布投降時,從未明確道歉與懺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透過「玉音放送」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然而,那份名為《終戰詔書》的宣言中,沒有一句道歉,更沒有對侵略與屠殺的懺悔之詞。裕仁以「戰局不利」、「原子彈殘酷」、「為避免國家滅亡」作為投降理由,哀悼的對象僅限於日本國內的戰死者與其家屬,對於亞洲其他國家在侵略戰爭中遭受的巨大損害,則隻字未提,更遑論承認罪責。這就是戰後日本歷史態度的起點:承認失敗,但拒絕承認罪責。
在國際壓力下,1995年,時任首相村山富市在戰後五十週年談話中明確使用「殖民統治與侵略」「痛切反省」「由衷道歉」等表述,這是日本戰後最具誠意的一次官方道歉。此後,小泉純一郎在2005年沿用類似措辭,但已開始淡化日本單方面的責任;2015年,安倍晉三更以「痛切反省」取代「由衷道歉」,並強調「後代無須背負道歉責任」,引發中國大陸、韓國等鄰國強烈批評。
到了今(2025)年,戰後八十週年,自民黨總裁、首相石破茂更是破天荒直接取消「戰後首相談話」,這是三十年來首次。此舉並非偶然,而是對黨內右翼勢力的妥協。自民黨保守派,特別是安倍派系,長年主張「歷史淡化」,甚至企圖推翻既有道歉表述。為鞏固權位,石破茂寧可切斷道歉傳統,也不願與右翼翻臉。
這一決定凸顯了日本社會在二戰加害責任上的根本問題:戰後八十年,許多日本人視戰爭責任為「歷史課題」而非現實義務,甚至將戰爭記憶等同於「受害史」,完全忽略自己曾是加害者。這種敘事偏差,使得軍國主義的陰影在教科書、媒體與政治輿論中不斷回潮。
與德國相比,對比更為鮮明。德國在戰後立即清算納粹罪行,公開承認大屠殺,立法禁止納粹言行,並將歷史反省制度化。從西德總理布朗德(Willy Brandt)在波蘭華沙猶太人遇難紀念碑前下跪,到德國總統魏茨澤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的演講,德國領導人的道歉具有連貫性與制度保障,形成了全社會共識。反觀日本,雖在外部壓力下偶有道歉,但缺乏制度化機制,一旦國際壓力減弱,右翼勢力便迅速反撲。
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除了民族性與國際壓力強弱不同外,還有一個關鍵,真正代表國家的最高象徵從未被究責。在總統制國家,是總統;在內閣制國家,是總理與象徵性的國家元首;而在君主制國家,自然包括君主本身。
日本的對外侵略,天皇從來不是局外人,而是戰爭的默許者與認同者。沒有天皇的批准,日本軍人不會接受無條件投降;而天皇在戰爭決策中的地位,讓他的責任毋庸置疑。日本國內認為天皇權威不可挑戰,因此拒絕讓天皇認錯,但對於受害者而言,唯有天皇的正式道歉與懺悔,才具有真正的歷史與道義意義。
歷史的債務,不會因時間流逝而自動結清;真正的和解,也不會在沉默與遺忘中誕生。因此,我主張,除了繼續對日本政府施壓,更應將責任直指日本天皇,要求其正式道歉與懺悔。只有當日本天皇親口向受害國與受害人民道歉,日本的政府與人民才會徹底正視並承擔應有的歷史責任,也唯有如此,亞洲的歷史傷口才有真正癒合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