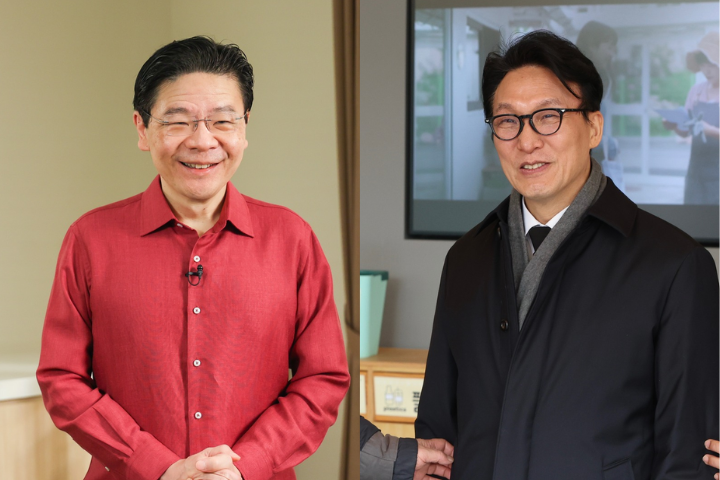魯云湘/政策與戰略研究員
每逢歷史轉折的紀念時間點,關於中國大陸改革初期領導人物的討論,總會重新浮現。其中,胡耀邦近年尤被高度懷念,常被視為良知與改革的象徵。但如果只從個人品格或道德高度來評價這段歷史,反而容易忽略改革實際是怎麼運作的,也看不清它為何從一開始就存在明顯的限制。
事實上,中國大陸在 1978 年後的改革開放,並非單一領導人意志的展現,而是一段由多位領導人分工推動、同時受到內外條件影響的集體轉向。若將胡耀邦、趙紫陽與鄧小平放在同一結構中橫向觀察,改革如何得以啟動、又為何最終被框定,便較為清晰。
胡耀邦所承擔的,是改革中最具風險的一環——歷史與道德的糾錯。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摘除政治身分標籤,不僅是政策調整,更是挑戰了既有政治正當性的傳統敘事。這為改革修補最基本的社會信任,卻也同時動搖既有權力結構的歷史基礎。問題在於,這種糾錯始終高度仰賴當時的政治空間與個人承擔,並沒有真正變成制度,因此從一開始就帶著不穩定的風險。
趙紫陽面對的,則是另一個更為技術性、卻同樣關鍵的問題:改革如何落地運作。從大陸安徽小崗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農村溫飽;到深圳等經濟特區的設立,把原本抽象的「對外開放」,變成可以實際操作、看得到效果的實驗;再到價格改革與地方試點,逐步推廣全國,這條「先試、再推、逐步擴散」的路徑,正是其在四川、廣東兩省主政經驗的全國化。
改革能夠啟動,也與外部環境密切相關。1979 年中美建交、對外開放窗口的出現,以及對既有計畫經濟模式可持續性的反思,使改革具備戰略與國際層面的正當性。然而,制度改革的深化,也迅速帶來通膨壓力、分配失衡與社會焦慮,改革開始同時製造新的不穩定來源。
正是在此背景下,鄧小平的角色逐漸浮現。與其說他單純是改革的推動者或阻礙者,不如說,他更像是在關鍵時刻,負責判斷改革風險能走到哪一步的最後把關者。在其判斷中,改革可以推進,但必須可控;可以試錯,但不能失序。當改革的社會成本與政治不確定性同步升高,踩下煞車便成為理性選擇。
改革的限度,並非只來自最高層的抉擇,也來自體制內部的理念分歧。以陳雲為代表的保守派,主張所謂的「鳥籠經濟」,也就是由國家計畫主導、市場只能在一定範圍內活動,對過快市場化可能引發的失序保持高度警惕。這使改革自始即處於「進兩步、退一步」的拉鋸狀態,而非單向的線性演進。
1987 年胡耀邦下野、1989 年趙紫陽失勢,正是改革走到風險臨界點時,體制選擇踩煞車的具體結果。它們不僅是政治事件,更象徵著改革在高風險狀態下被重新框定。改革並未被全面否定,但其邊界被清楚劃出。
從長期視角看,改革所帶來的腐敗問題、貧富差距擴大,以及大量農民工湧入城市,形塑了持續至今的社會焦慮,也深刻影響了後來體制對穩定的高度重視。某種程度上,近年強調國家角色的政策取向,以及「共同富裕」、「國進民退」等討論,皆可視為改革年代風險記憶的延續。
若從比較視角觀之,中國大陸改革的路徑,與台灣地區在相近時期所經歷的轉型,存在本質差異。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更多是一種體制內部為維持運作與正當性的自我修補;而台灣自 1980 年代後期起的轉型,則是由下而上的社會力量持續衝擊,迫使體制進行讓步與轉型。如經國先生施行的改革,正是在經濟放鬆與政治解嚴之間逐步釋放空間,使制度轉型得以向社會層面延伸。
由此回看,胡耀邦之所以被中國大陸的社會懷念,正因其道德糾錯未被制度承接;趙紫陽令人惋惜,在於制度化改革尚未完成政治保險;而鄧小平之所以成為定錨者,則因其代表體制最終選擇穩定優先。
改革並不是被中止,而是在風險考量下,被清楚地限定了邊界。理解這一點,或許比情緒性的懷念或否定,更接近那個年代的真實,也更有助於我們理解不同社會在轉型壓力下所做出的制度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