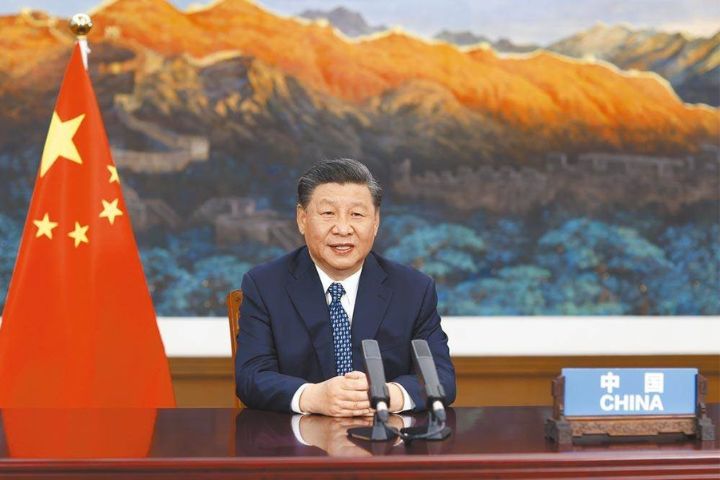民眾黨主席黃國昌繼上次到政治、東吳大學與學生座談後,17日晚間來到文化大學,與國民黨立委吳宗憲合體開講,並同步在個人Youtube頻道直播。講座上半場,黃國昌以「過來人」的身份感性分享其從18歲爭取學權的心路歷程,細數當年對抗「特別權力關係」與軍訓必修制度的艱辛往事,揭示了抗爭之路的孤獨與挫折,並勉勵年輕學子,在摸索人生道路時應選擇「有生命意義」的事,會相當有成就感。
文化大學學生會舉辦「打開國會之門:政策、制度與爭權的對話」講座,並邀請黃國昌與吳宗憲與年輕學子展開一場深度對話。黃國昌透露,主辦單位給他3個主軸題目,包括國會內的工作、社運及學生權益爭取。他說,「因為前幾場在其他大學的演講,開放給同學問問題,對於時事、政治關心的比較多,但是在學校裡面演講的主題,他希望盡量不談政治」。
黃國昌會這樣說,是因為他希望當走入校園的時候,分享給大家的是走過的人生道路,可能有迷惘、摸索與跌倒,並從中成長,這些經驗對於年輕學子摸索道路時,若能受到啟發,他覺得會不虛此行。
從18歲到52歲:為何仍為理想成為「被告」
接著他指出,前陣子到台北地檢署應訊,身分是被告、嫌疑犯,也就是吳宗憲以前要打擊的對象,他8月30日舉辦公民走讀,走到兩廳院(他那個年代稱中正廟),走到愛國西路跟中山南路口時,整片道路被警察圍起來,並僵持不下,曬太陽曬了7個小時,體感溫度40度,最後被以違反集會遊行法移送法辦。
「我是失敗的人還是成功的人?如果按照我當年的學經歷,我做不一樣的選擇的話,今天最起碼是部長」。黃國昌說,他今年52歲,從北檢走出來後,他自問為什麼52歲了,還因為違反集會遊行法到北檢接受調查,最後竟成被告,「從18歲到52歲,這34年人生我做了什麼?為什麼到了52歲還在做年輕時候的事情?」
立法院12月8日召開「重塑大學自治與校園民主—《大學法》修法與高教治理改革之檢討及策進」公聽會,黃國昌提到,他那天忙到不行,但一定要到場,「在最後一個人發言結束前,還我趕到了」。
挑戰「特別權力關係」
為什麼這場公聽會如此重要?黃國昌說,這是他的青春,1991年進台大法律系,最高法院判決,國立台灣大學與學生之關係為管理與服從、教學與學習之特別權力關係,應循其管理;監督之特別權力關係謀求救濟、不屬普通法院審判之範圍。
憑什麼我的受教權受到侵害不能向法院尋求救濟?反而變成監獄跟受刑人關係?特別權力關係特別在哪裡?黃國昌接著提到1993年10月14日,他大三當台大學生會長,是課業最繁重的一年,但他只上了6個小時的法律課,因為他都在弄《大學法》,當時在爭軍訓護理課,軍訓不及格要延畢,但當時絕大數人都沒在聽課。
「可能是那時候黑熊學院概念還沒有很流行!現在或許大家會聚精會神聆聽!」黃國昌認為,從國家制度來看,要思考一群人浪費時間資源空間甚至電燈的錢,在所謂追求真理的大學殿堂進行毫無意義的活動。
其次,為什麼軍訓一定要修且要修2年,是誰決定?黃國昌表示,原來是教育部決定,《憲法》不是保障大學自治,憑什麼教育部把手伸到大學裡去,所有男生必修否則不能畢業,答案竟是要光復大陸國土,「1991年還會這樣想的人大概進入幻想的境界了」。
對於大學自治是教授還是學生決定?黃國昌說,他也當過教授,立場會是教授決定,學生只是過客;但學生會認為學生才是學校、教育的主體。也因此,大學自治的概念就會發現複雜的權力關係,一個是國家跟大學,另一個是內部的權力分配,最代表的就是校務會議決議,比校長講得還重要,但會不會之後有瘋狂的校長不公布校務會議決議他不知道。
黃國昌說,但2025的台灣還有什麼是不可能發生,就連總統賴清德都可以不公布法律了,校長為什麼不可以,他拭目以待,看有沒有比萊爾校長更狂的校長出現,引發台下學子哄堂大笑。
抗爭者的孤獨:在「壞學生」標籤與同儕不解中前行
接著,黃國昌續指,了解了權力關係後,教授跟學生變成夥伴關係,要抗議教育黑手伸進,並提及,1993年、21歲的他首次衝立法院,因為《大學法》,但經驗不足沒有真的衝進去,要經過議場大門時被警察攔下,最終沒有成功,卻也爭到學生可以出席(原是列席)校務會議,看起來是重大勝利,但卻沒有保障學生最低代表比例,所以當時很氣那群立委。
黃國昌進一步指出,當年身為會長,他辦了有史以來第一次公民投票,理由為「軍訓護理課是否改為選修?」一個學生一票大家都可以投,卻被大部分老師說「法律系課都不來,不好好念書,一天到晚搞學生運動,叛亂分子,典型大學畢業加入民進黨選國大代表」。
「那群老師是這樣在看我的!」黃國昌說,當年辦了這個投票,承受極大壓力,甚至不小心參加鴻門宴。接著說,《大學法》修正以後,回台大參加校務會議,真槍實彈討論,一開會他就問「校長,我是列席還是出席?」校長說「你是列席代表」,他當場憤而拍桌,《大學法》已經三讀通過,當時的總統、行政院長沒有不副署,校務會議應有學生代表出席,結果,校長再次說:「你是列席代表,你沒有資格發言,再吵就請人把你轟出來」。
「我現在就出去,因為你們現在是非法的校務會議!」黃國昌當時這樣說,又為了這場校務會議在台灣大學行政大樓外睡了三天,當時還綁了兩個布條「大學改革作先鋒、台大精神永留存」,因此與當時學生集結在外面開了一場臨時的校務會議,這是當年在學校爭取學權的抗爭。
他也坦言,抗爭當然有付出代價,所有老師都覺得他是不用功的法律系學生,是顛覆校園的壞學生,差點被開除。大三那年卸任學生會長,疲憊不堪、傷痕累累,難過的是回到法律系,系上同學完全不在乎他在做什麼,覺得考上律師、司法官比較重要,怎麼會搞這些事?「你以為你在幫忙他們爭取權益,結果他們根本不在意,那失落的感覺讓我身心俱疲,感到重創」。
遲來的公道:大法官釋憲與「最甜蜜的復仇」
因此大四那年,他躲在法學院以外的空間,把以前荒廢的學院找回來,每天早上八點圖書館報到、十點離開,後來發現時間太短,最後去台大醫學院圖K書中心讀書,直到畢業前夕,他看到一則新聞,1995年5月大法官蘇俊雄作380號解釋,教育部訂共同必修科目表違憲,他看到這則新聞當場落淚,「我在大學那一年終於找到了公道,終於證明我們講的是對的」。
隔月382號解釋,學校對學生退學或類似處分,可以向法院尋求救濟,特別權力關係崩壞,「搞了4年,他們說的事情是對的,沒有相信行政法教科書所說的鬼話,最後成為我們的憲法價值」。若大學能重來是否還會選擇同樣的抗爭經歷?黃國昌坦言,理智上我不知道,但他嚴重懷疑他會再做一次一模一樣的事情,大學畢業那年,等到這兩件事情,一切都值得了。
黃國昌透露,他做過最甜蜜的復仇是大學畢業那年,考上律師司法官,只想要那些老師知道,他做這些事情,是有意義的,且做這些事情的人不是壞學生,他只想證明這件事。後來當時台大校長陳維昭知道他考上律師司法官嚇到下巴快掉下來了,因為當時衝突真的很激烈,激烈到他出回憶錄還在文中罵他,但他不怪他,因為當時各有立場。
傳承制度改革、勉勵學子追求生命意義
「在爭取學權這條路上很累」,黃國昌說,在做學運時,最討厭別人指手畫腳,所以後來離學運都保持友善距離,但他提到有一個案子很有趣,2010年一名萬能科技大學生成立一個社團叫「邊緣之聲」,讓學校很不開心,為什麼不能中立而是要邊緣?因此禁止他成立。
後來該名學生跑到校門口靜坐抗議,換來的卻是退學,後來就幫這群學生當訴願代理人,跟教育部訴願,委員會開會還出席,最後成功,退學處分撤銷,丟回去學校重新處分,同樣結果是退學,後來該名學生就不讀了,沒再提訴願。
「因為有這些故事存在,所以我們才要在意,因為你不知道下一個人是誰!」黃國昌表示,在制度上面如何防止這類事情發生,這就是我們的責任,也就是立法委員。但學生自己也要在意,你們不在意,立委也不會在意。
最後,黃國昌也勉勵台下學子,以後找工作要選自己會「開心」的事情,他認為是生命有意義的,能夠創造一些改變的,讓下一代跟你身處的時代比起來,能夠更像一個人一樣活著,追求人生目標跟理想,不會像前述所說的,只想成立邊緣社團就被開除。不管是學校內部、走入社運與政治,不同角色上,創造制度的改變,會很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