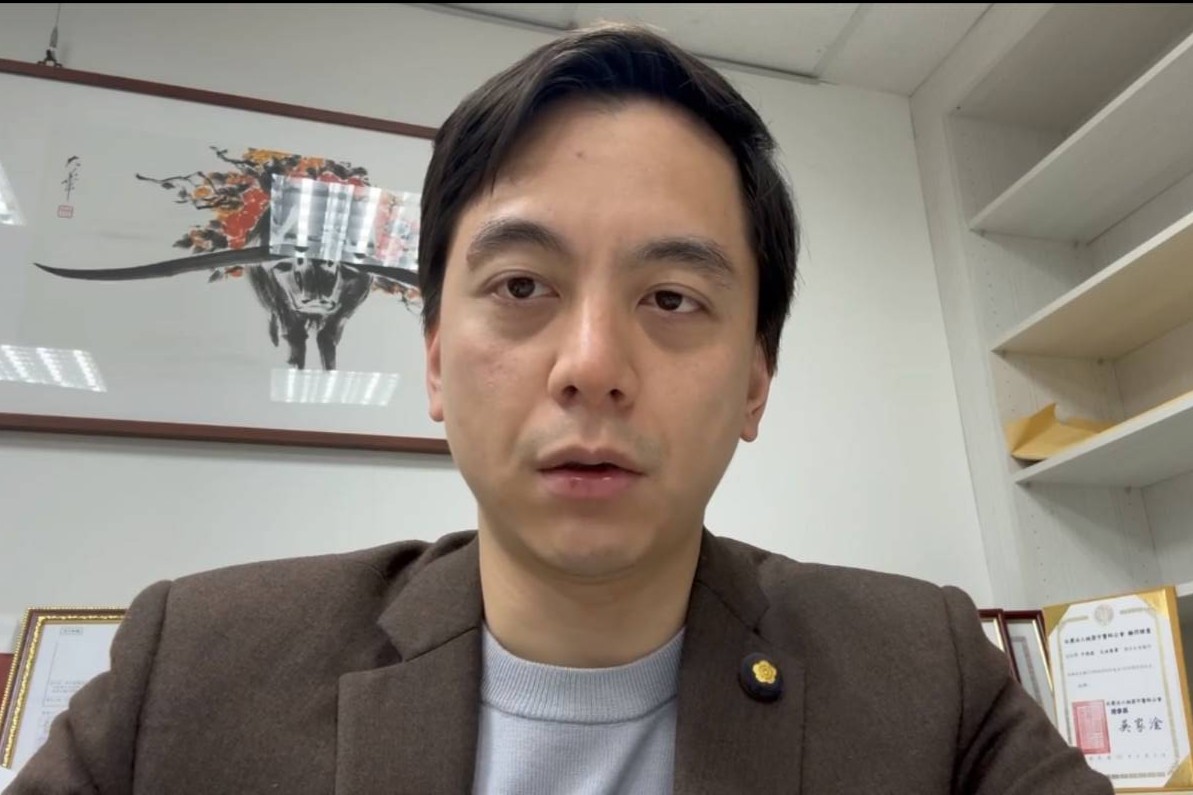李明/政大外交系兼任教授、中美文經協會秘書長
據「日經亞洲」報導,我國原準備在波羅的海三小國之一的愛沙尼亞首都塔林(Tallinn)設置代表處,卻已陷入停滯。據透露,卡關癥結在於台北堅持使用「台灣」(Taiwanese)之名,而塔林方面則因忌憚北京反彈,堅持沿用國際慣例「台北」(Taipei)的稱呼,關鍵是賴政府覺得不爽、拒不答應。
這次事件,說明民進黨基於獨派立場,將駐外機構從原來較中性的台北(Taipei)代表我國,偷換為以「台灣」、「台灣人」、或「台灣的」稱呼滑向「台獨」的圖謀。賴清德總統負責國防、外交和兩岸事務,理當是外交政策最終決策者,必須為這件事負起責任。而行政院長卓榮泰和外交部長林佳龍等一干大小官員,則是賴的部屬,亦是難辭其咎。
我國自1971年退出聯合國以來,國際環境深受北京壓迫,接連退出許多國際組織而由中共接手。再者,中共積極在各地挖走我邦交國,使我接連和多國斷交,駐外使領館一個個關閉。我撤館館員或尚有餘裕在限定時間內撤離,較差的情況則是被要求在48小時內,或立即離境,可謂尊嚴盡失。
1979中美建交《台灣關係法》界定台美關係
也正是1971年7月,美國國務卿季辛吉秘訪北京,開啟中美建交的進程。1972年再以《上海公報》作為基礎繼續推進,最終在1979年1月1日雙方建交。當時的卡特政府對台灣極不友善,幸美國國會兩黨議員基於義憤,草擬「台灣關係法」逼使卡特就範,以適當界定台美關係。
卡特政府當時給台灣代表處名稱「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CCNAA)」極為拗口,外人甚至無從察覺那是台灣的代表機構。直至多年後台美關係改善,1994年才更名為「台北商務文化代表處(TECRO)」。這些過程極為苦澀,顯示中華民國外交的險阻,也說明外交人員除艱辛奮戰,更要堅韌務實,以維護國家利益。
至於我國與外國經濟合作,常是希望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但我國交涉的對象國常有政治考量,特別是必須兼顧和北京關係,經常以「經濟合作協定」或「經濟夥伴協定」代替。我國第一個FTA是與中美洲的巴拿馬,簽訂於2003年8月;另有瓜地馬拉(2006年)、尼加拉瓜(2006年)、薩爾瓦多和宏都拉斯,多數國家至今仍維持,但尼加拉瓜在2021年12月和中共建交,單方面宣布終止。
早在2002年陳水扁政府便想和新加坡簽訂FTA,但陳水扁擬用Taiwan名義,新加坡則顧慮到「一中原則」,卡關相當長時間直到2010年馬英九政府與北京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在北京默許下,台灣得以「個別關稅領域身分」與他國簽訂FTA。2011年新加坡始與台灣談判,2013年11月簽訂「新加坡與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經濟合作協定」(ASTEP)。新加坡當時更是基於「協定必須低調、務實和穩定推進」,我國依此因應,實為務實外交最佳註解。
立陶宛「台灣代表處」做法未必務實
媒體分析,台灣想比照2021年蔡英文時代,台灣與立陶宛在首都維爾紐斯(Vilnius)成功設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的模式,在愛沙尼亞複製「台灣代表處」。民進黨政府的心思,為希望再一次彰顯台灣的「主權身分」。不過,賴政府的外交作為,卻造成愛沙尼亞極大困擾,它要擔心北京在雙方仍有外交關係的狀態下,將施行哪些報復行動。
當年北京為了報復立陶宛,不僅將雙邊關係降為「代辦級」驅逐大使,更在海關系統將立陶宛除名,變相施行經濟制裁。北京更向德國等歐盟企業施壓,要求他們停止使用立陶宛供應商的零組件,否則將失去中國大陸市場的准入權利。歐盟向北京提出抗議,最終北京才逐漸放鬆了對立陶宛的報復行動。
2024年10月立陶宛國會大選,由反對黨「社會民主黨」勝出,新政府首腦直言,允許以「台灣」名義在立陶宛設立代表處是一項「重大的外交錯誤」。因此我國駐立陶宛代表處,隨時可能因執政黨輪替被迫再度改名。
立陶宛國土面積約6.5萬平方公里,人口約292萬人,與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並稱「波羅的海三小國」。相形下,愛沙尼亞地理位置更重要,它國土地僅4.5萬平方公里,人口更僅有136萬人,卻位於波羅的海最北端,隔芬蘭灣與芬蘭相望,東與俄羅斯接壤,南鄰拉脫維亞,等於控制了芬蘭灣俄羅斯出海口。俄國對愛沙尼亞戰略地位相當重視,特別是現在處於俄烏戰爭關鍵時刻,中共則支持俄國在歐洲的利益,自然盯住愛沙尼亞和台灣的交往。
自蔡英文時代的2017年開始,我國在奈及利亞、巴林、厄瓜多、杜拜和約旦等5國館處被北京要求改名並且得逞。2023年我駐斐濟代表處「正名」的努力,也以失敗收場。最近一次是2025年我駐南非代表處官網名稱被改為「台北商務辦事處」,甚至遭南非政府要求代表處搬離首都。
林佳龍空講務實外交
外長林佳龍雖說將以「務實外交」處理設館事宜,但他又抬出「台灣與愛沙尼亞有共同的民主與人權價值觀」,顯然文不對題,何來「務實」?我方要求「台灣」作為設館名稱,愛沙尼亞有其困難,我國怎能一味強求再蹉跎時機?
無論是我國顛簸的外交過往,還是建立FTA的辛苦經驗,可以提供外交部門在愛沙尼亞設館過程的參照。台灣究竟要在館處命名上見樹不見林,繼續堅持己見;還是接受傳統上使用「台北」的務實作法,先設置代表處,強化與愛沙尼亞實質關係?兩種不同思考,成敗得失高下立判。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