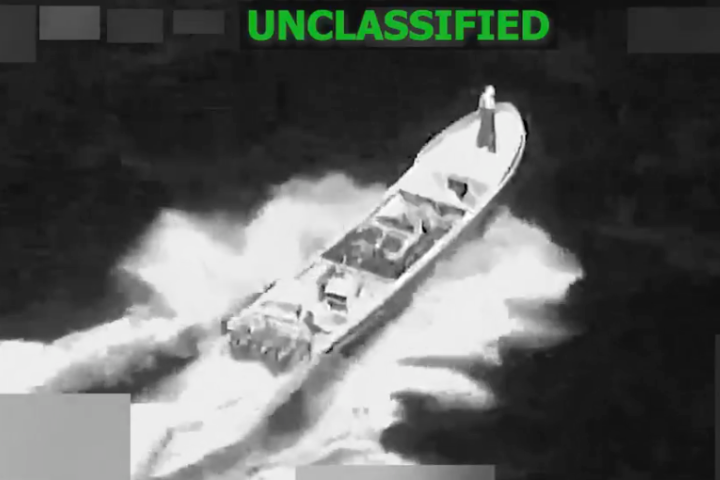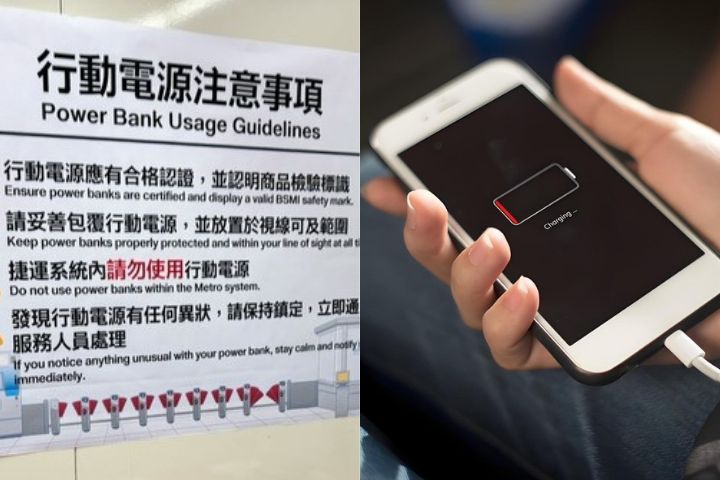陳國祥/資深媒體人
日本經濟困境深重,體制病症沉痾,社會結構僵化嚴重制約經濟。高市早苗以「日本再度旭日東升」為口號,成為自民黨首位女性總裁,並可能是日本第一位女首相。但她的勝利更多是象徵性的政治轉向,而非經濟結構的突破。日本社會對她寄予厚望,期盼她能擺脫「失落三十年」的陰影,讓日本重返榮光。從她的政策藍圖來看,無論是經濟思維的舊套,還是改革手段的保守,都未見治症良方,因此期盼可能要落空。
高市早苗的崛起,是民族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勝利。她繼承安倍晉三的「強國路線」,主張修改憲法、強化防衛、振興民族精神,並以「去戰敗國化」為號召。然而,這種意識形態的強調,並不能帶來具體的經濟成長。當她大談「強軍復興」與「精神獨立」時,日本民眾最關心的仍是實質薪資停滯、物價上漲與生活成本飆升的問題。
高市提出的經濟政策不外乎幾項:減稅、發放現金、廢除臨時汽油稅、擴大企業研發抵免。這些措施多屬短期刺激,缺乏長期結構改革。她所謂的「財政重組」更偏向保守收縮,而非投資未來。相較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財政刺激、貨幣寬鬆、結構改革),高市的版本既沒有明確的策略重點,也缺乏突破既得利益的決心。在她的政策框架裡,「國家自尊」凌駕於「國家競爭力」,「精神重建」取代「經濟重建」。這種政治取向,或許能凝聚右派支持,但卻無法應對逆全球化時代的經濟挑戰。
日本經濟長期停滯,並非單一政策所致,而是多重結構性問題疊加的結果。首先是少子高齡化。日本生育率長年徘徊在1.3以下,高齡人口占比已超過28%,導致勞動力萎縮、消費力下降。企業難以招工,年輕世代因薪資低、租金高而不敢結婚生子,形成惡性循環。高市強調「家庭價值」,卻反對女性主導職場、限制移民政策,等於自我設限。她的社會觀念過於保守,不利於改善人口結構。
其次是創新乏力與產業空洞化。自泡沫經濟崩潰以來,日本企業普遍採取保守經營策略。終身雇用制與年功序列制讓企業缺乏人力彈性,年輕人難以創業或轉職。風險投資市場規模遠遜美國、中國與韓國,創新生態薄弱。製造業外移又導致技術與人才流失,產業鏈斷裂。即便日本企業仍握有巨額現金儲備,卻不願投資新技術,只追求財報穩定。高市若不打破這種「財務保守主義」,任何產業政策都只是紙上談兵。她雖口頭支持創新與數位化,但未提出具體制度改革方案,例如如何改善風險投資環境、如何改革企業治理結構。
十年前,安倍晉三曾以「三支箭」提振日本經濟,但真正落實的僅有貨幣寬鬆與財政刺激;結構性改革那支箭始終未發射。如今的日本經濟,正是當年「改革半途而廢」的後果。長期的零利率與量化寬鬆(QQE)雖支撐了資本市場,卻扭曲了資源配置,使企業與銀行形成「低效率共存」的病態平衡。貨幣寬鬆反而養出了「殭屍企業」與「懶惰資金」,投資報酬率持續下滑。
日本內閣府統計顯示,近十年GDP年增率多在1%上下浮動,遠低於美歐主要經濟體。2024年甚至出現技術性衰退。高市若僅延續這種寬鬆思維,而無法引入結構調整與市場改革,日本將繼續在低成長、低通膨、低信心的三重陷阱中徘徊。
日本政府債務總額已達GDP兩倍以上,是全球最嚴重的主權負債國。雖然多由國內投資者持有,尚未引發外資信任危機,但政府每年龐大的利息與社會保險支出,幾乎吃掉一半預算,削弱了任何積極政策的空間。高市主張「財政重組」,意在減少無效支出、提升效率。然而,在老齡化社會中,削減醫療與退休金開支幾乎不可能。若僅靠削支撙節,反而會壓抑內需;若加稅,又將進一步削弱消費。她若無法在財政「加法」上找到創新突破,如稅制誘因、科技研發補助或青年創業減稅,則其財政重組只是形式上的平衡遊戲。
日圓貶值與通膨壓力是失衡的雙刃劍。日圓持續走貶,短期有利出口,卻推高進口成本。能源、食品價格飆升,民眾生活負擔沉重。這種「輸入型通膨」並非真正的景氣復甦,而是結構性脆弱的反映。2024年春鬥中企業雖普遍調薪3%以上,看似薪資回暖,但物價漲幅更快,實質購買力反而下降。若高市無法在勞動市場改革、提高生產率與增加可支配收入上取得進展,「通膨假象」將很快崩潰。
面對新能源、半導體、電動車、人工智慧等全球新產業競爭,日本本應憑藉技術底蘊重奪一席之地。高市也曾宣示要讓日本在「固態電池革命」中領跑,但她的產業政策更像政治宣言,而非具體行動方案。在全球供應鏈重組的浪潮中,日本企業亟需整合政府、科研機構與產業資源,縮短研發轉化周期。然而高市並未提出如何建立「產學研聯動」的長期機制。她強調「日本技術+本地製造」的海外合作,但忽略了國內創新基礎薄弱、人才流失的現實。缺乏清晰的產業戰略,日本將繼續被中韓美三方壓縮競爭空間。即便固態電池或氫能等新技術取得進展,也難以迅速轉化為就業與內需成長。
高市在社會議題上極為保守。她反對同性婚姻、限制性別平權政策、強調家庭角色與民族傳統。這種立場或許能迎合保守選民,但卻與經濟現實背道而馳。日本若要解決少子化與勞動力短缺,就必須鼓勵女性充分參與職場,開放外籍勞工,並創造更具包容性的工作制度。然而高市的價值觀傾向於「回歸家庭」與「文化純化」,這不僅無助於提升生產力,反而可能進一步縮小勞動人口。她想恢復「戰後前的日本精神」,卻忽視現代經濟的開放性、流動性與多元性。結果可以預見,日本不僅在產業上老化依舊,在社會觀念上也將更封閉。
日本的真正問題不是缺乏刺激措施,而是缺乏長期改革意志。高市早苗若只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行進,將重演安倍第二任初期的悲劇:政治高調,經濟無為。當前日本最需要的,不是象徵意義的「女性首相」,也不是復古式的「保守振興」,而是一場深層結構重建:必須打破終身雇用與年功序列,釋放人力市場活力;必須改革稅制與企業治理,鼓勵創新與風險投資;必須開放移民與性別平權,擴大勞動參與率;更必須以長期法制化的方式推動產業轉型與教育改革。若無這些根本性改變,任何新首相都只是延續停滯的輪迴。
高市早苗或許能讓日本「精神昂揚」,卻難讓日本經濟再度崛起。在民族浪漫與經濟現實的夾縫中,她最終恐怕也只能成為「失落三十年」的又一位見證者,而非終結者。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