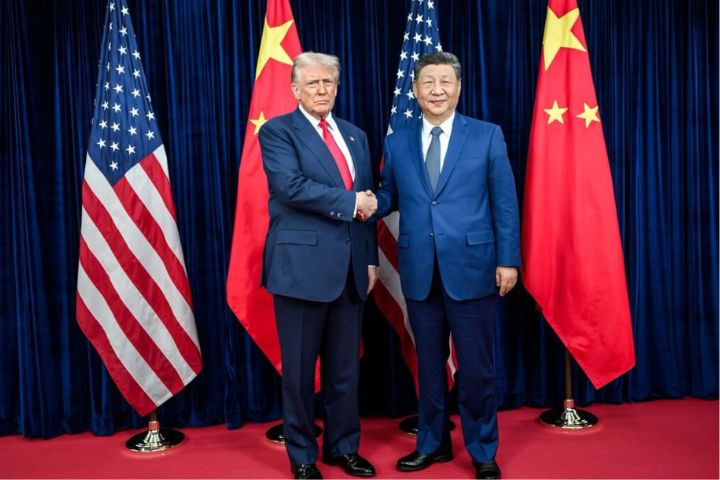在大陸經濟進入調整轉型之際,一場關於「究竟靠什麼帶動中國下階段成長」的辯論,在學界與輿論場悄然升溫。香港科大教授金刻羽日前與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的觀點,引發關注。兩人對大陸應以「消費」或「投資」作為未來發展核心動力看法南轅北轍,亦反應大陸多年來經濟結構的矛盾。
近年,大陸已明確將提振內需、刺激消費列為「2025年首要任務」。這不只是短期政策任務,更象徵大陸經濟試圖從長期依賴投資驅動、出口導向的發展路徑,走向以國內市場為主、居民消費為核心的重大轉型。但從理論到現實,內部利益結構與地方發展慣性,早讓「要消費,還是要投資」成為各界拉扯的焦點。
富裕國家都靠消費:金刻羽點出結構根本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金刻羽最近在一次公開論壇中強調,中國可大談科技競爭、人工智慧及基礎設施建設,但除非中國真正成為一個以居民消費驅動的國家,否則永遠無法邁入富裕行列。
她舉例說明,從全球發展經驗看,能躋身已開發國家的幾乎都是典型的消費大國,同時也是社會相對公平、生活幸福的國家。相較之下,如果一個國家長期偏重生產與投資,卻忽略分配、公平與居民收入的成長,即便產能驚人,也終究難以實現普遍繁榮。
金刻羽表示,中國的政治與經濟治理體系仍明顯以生產為主要導向,地方政府績效多圍繞GDP與工業投資規模展開競爭。她認為,如果未來能將消費指標納入政績考核體系,讓地方領導者以促進居民消費、改善生活品質為自我評比的重要依據,那將會是中國從舊有產業鏈走向新經濟形態的關鍵一步。這種轉型不只意味經濟面貌改變,也代表整個治理思維和社會價值重心的調整。
就業與服務業是關鍵:給年輕世代機會
另一個她反覆強調的重要理由,則與中國與全球互動結構密切相關。金刻羽認為,中國持續將大量產品出口至國外,表面上是供應鏈效率的體現,但長遠看卻導致全球其他國家難以發展同樣的產業能力。
她強調,若中國成為更強大消費市場,就能給其他國家更多機會參與全球供應鏈,與世界建立更健康的互賴與平衡。從這角度看,消費並不只是中國內部的發展問題,也攸關其如何被全球接納並共同繁榮。
在談到促進消費實際條件時,金刻羽將焦點放在中國就業結構缺陷。她直言,就業是所有消費的基礎,但目前中國服務業僅吸納約47%就業人口,對GDP的貢獻僅約一半,相較已開發國家仍有顯著差距。
年輕人越來越重視生活與工作平衡,他們追求在地化的消費體驗與生活型態,不是一味投入工廠生產。金刻羽強調,未來若能在二、三線城市創造更多服務業與新型經濟的工作機會,不但可支撐收入增長,也會反過來刺激新的內需浪潮,進而為科技創新提供持續的商業場景與市場。
余永定力挺基建投資:短期穩增長可控性強
與金刻羽的立場幾乎相反,余永定則持續堅守「基礎設施投資」才是中國經濟首要推進力的主張。作為曾經的央行決策圈核心成員,余永定提出的理據具有很強制度與傳統政策思維。他承認發放消費券、推動「以舊換新」等措施確實可短期刺激需求,但質疑其作用的持久性與規模。

他認為,要真正避免陷入「收入要靠消費拉動,消費又得靠收入提升」的循環邏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讓政府主導融資投入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從而創造初級收入,繼而帶動二次投資與消費。
在余永定學術認知中,基礎設施投資不僅能迅速產生顯性經濟增量,還因屬於可由政府直接掌控的變數,具備強大的調控便捷性與可操作性。他列舉研究機構資料指出,中國未來5年在公共投資方面仍至少有約31兆元(人民幣,下同)的空間,其中光是城市地下管網建設就可能需要4.5兆元。
他甚至主張,中國完全可在「十五五」規劃期內重新推動一批類似2008年四兆元計畫的超大型專案,如在西部地區延伸經濟走廊至中亞,既能化解內部產能壓力,也有助於地緣戰略布局。
投資思維的隱憂:結構失衡與內卷困境
儘管如此,輿論與多數獨立經濟學者似明顯更傾向金刻羽觀點。原因並不難理解。中國當前的經濟困境,根源在投資率長期過高、消費率顯著偏低所帶來的結構性失衡。大量投資雖然在早期迅速積累了驚人產能,卻也埋下今天各行業「內卷」、過度競爭的種子。過去20年,中國居民收入佔GDP比重反而持續下降,正說明過度依賴投資並不能穩健提升民眾購買力。
同時,基礎設施投資多屬資本密集型項目,其實際帶動就業的能力有限,很難像服務業一樣廣泛吸納勞動力。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中國投資規模屢創高峰的同時,就業市場和收入信心卻沒相應水漲船高。更多學者甚至警告,若產能已明顯過剩,繼續以投資擴張作為首選,只會讓壓力往後堆積,終究得回到如何讓產品賣得出去、讓居民敢於消費的根本問題。
《觀察者網》在報導這場學界大論戰時也說,這些現象在理論層面上早有前人揭示。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危機時便指出,真正的危機往往不是絕對生產過剩,而是勞動群眾缺乏足夠支付能力所導致的「相對過剩」。凱恩斯則以「節約悖論」提醒,如果全社會都因擔憂未來而選擇增加儲蓄、削減開支,國民收入將反向萎縮,經濟更易步入衰退。
當提振消費被正式納入國家中長期規劃的首要任務,這場關於中國經濟路向的辯論勢必還會持續很長時間。無論最終採取什麼政策組合,如何真正強化居民收入與社會保障體系,讓廣大民眾有意願、有能力安心花錢,恐怕才是化解投資與消費結構性失衡的根本解答。